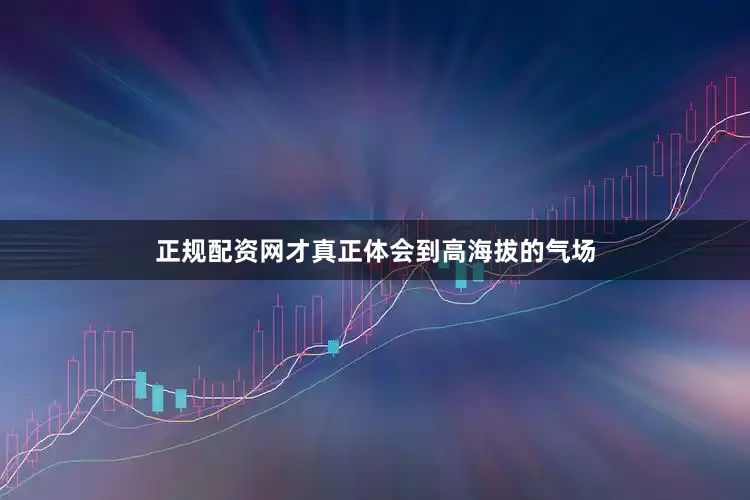
一
2025年8月6日中午,我来到日喀则,才真正体会到高海拔的气场。
在成都,生存法则是如何填饱肚子,如何打造财富阶梯,但到了这里,生存法则的第一条就是不能缺氧。
接下来的几天,每次往高处爬几步,就不得不停下来,像是有人用厚厚的布捂住了我的口鼻,胸口沉重得像压了块石头。我只能张开嘴,用力地把空气抽进肺里,但每一次吸气都感觉只填了一半。
我以前认识一位驻藏十几年的朋友。他告诉我,在这儿呆过两年以上的,几乎没人能完全躲过高反的后续影响。几乎个个都逃不掉高血压、心脏变大。高原缺氧,身体不得不制造更多的红细胞来代偿,血液变得黏稠,心脏负荷越来越重。
在高原,感冒从来不是小病。一旦得了,如果没有立刻处理、及时用药,很快就会转成肺水肿。肺水肿若再拖下去,便会急速进展为脑水肿,就是脑积水。
展开剩余93%一路忍着高反,在日喀则的噶东镇,我遇到了54岁的扎西。
他是典型的半农半牧的藏家人,一家整整十四口人。上有四位老人,下有八个子女。
全家有七十多亩地,作物只有一季收成,种的是青稞、土豆、小麦和萝卜。小麦和萝卜基本用来自给自足,青稞和土豆是唯一能换钱的作物,一年忙到头,农业收入差不多三万块。
他家里还有六百只羊、十头牦牛。
扎西解释说,这些羊和牦牛,其实是十五户家庭合伙放养的,不是他一家的。买一只羊羔就要一千块,养大之后能卖一千五。
听完扎西的介绍,我心里粗略算了一下,从羊羔长到成羊出栏,差不多要一年。按每只净赚五百来算,这十五个家庭平均每年从牧业中获得的收入,大约两万元。
牦牛生长周期更长,收益摊到每家,其实增加不了多少。好在羊群每年能新添一百多只羊羔,算是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一点盼头。
关键是,账不能这么算,在日喀则嘎东镇,一个家庭要生存下来,底线是有100头羊提供肉食,5头牦牛提供牛奶,还得有20亩青稞地、10亩小麦地,这是在高寒地区生存下来的必要物质条件。
这样的生活,哪来的“高收入神话”?
网络上那些牧民高收入的段子和图片,真不足以概括牧民的现实状况。至少我在西藏的调研过程中,没有遇到过。
扎西说,本地的牧民只有5%左右。
根据官方数据,2024年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3.2万元,其中城镇居民收入4.5万元,农村居民仅1.8万元 。
比如巴扎乡的次片(女主名)一家,为了盖房,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建成,总花费20万左右。砖石木料靠自己备,人工靠亲友帮衬,真正要花钱的只有家具、装饰和玻璃这些。
可能也会有极少数靠大规模养殖赚到钱,但对于大部分西藏的农牧民来说,收入其实并不高。
与收入相反的,是这里的物价,甚至高过一线城市。
在拉萨一壶甜茶26元,一碗藏面15元(不超过一两)。日喀则的物价往往比拉萨还要贵一些,因为它是中国最偏远的城市之一。
这里没有东部丰富的产业带,一般来说,越是边远之地,物资转运越艰难,物价往往飞涨,比如从甘肃、四川运钢材进藏,价格往往翻一番。
政府能做的,就是尽可能的给藏族同胞托底,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方面会比内地托得高一些。但这仍改变不了大多数农牧民收入有限、生活成本高的现实。
聊到这里,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结论。地理条件和产业链差距就摆在这,运输成本这道坎,很多业态都难以跨过去。
但有的时候,总会有新的事物跳出来,挑战你的认知。
这些年我国内国外跑了很多地方,形成了一个习惯,无论走到哪里,首先是去当地市场和超市看一眼物价。
我在日喀则调研的三天里,先后去过两家超市,一家是普通超市,一家是次片大姐推荐的。相同的采购清单,分别花了208元和172元,相差整整36元。
我特意比对了这家超市和成都同类商品的价格,发现只有略微上浮,有的比如劲酒甚至跟成都的价格持平。
所以在这次西藏调研篇之后,决定追加一篇,专门来聊聊这种“消费平权”背后的逻辑。
二
中国的地图像一只雄鸡,东部沿海是丰满的胸膛,西部内陆是瘦弱的脊背。
经济的血脉,长期在这片土地上分布不均。
从京杭大运河时代开始,东部就凭借水运之利、盐铁商业,奠定了千年繁华的基础。
改革开放之后,沿海地区更是凭借港口优势、外资涌入、政策试点,率先融入了全球产业链。长三角、珠三角逐渐成为世界工厂,也成了中国消费最活跃、最前沿的试验场。
胡焕庸线从黑河拉到腾冲,线东南占全国43%的土地,养活了94%的人口,也创造了绝大多数消费。物流、资金流、商品流,大多沿着这条线的右侧流动。
而左侧,长期处于商业的“低光照区”。很多县镇的老百姓,直到2010年之后,才真正接触到全国连锁的超市品牌。
换句话说,西部的消费者,长期以来一直在为“地域劣势”默默付费。消费,在这片土地上,从来就不是平等的。
中国消费市场四十余年,本质是一部由东向西、由城入乡的渗透史。
如今的中国,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,产能不是问题。问题在于,货如何高效、便宜、不变质地从流水线进入百姓家。
中国消费市场的二元结构,是一个被地理、物流、渠道、成本层层锁定的复杂系统。
传统多层分销模式,像一根臃肿的血管。每经过一层,价格就涨一次。到偏远地区,涨幅往往超过30%。以前,这叫“渠道成本”,今天,我们叫它“地域税”。
而消费平权的本质,就是推翻这座税山。
消费平权的真正使命,不是让上海和纽约看齐,而是让甘肃县城和成都市区,在基础民生消费上,逐渐看齐。
这条路很长,很难。但它一定值得!
如果说,消费平权在过去,因为地理决定了命运,那么,科技和模式一定可以改变这种命运。
中国是技术平权的试验场。比如曾经百万豪车专属的“主动变道、自动上下匝道、城市道路领航”等高阶智能驾驶功能,如今已标配在一些起售价仅10-15万元的国产车型上。
一个普通城市的年轻白领或小镇青年,通过购买一台经济型国产车,就能获得过去堪比豪车的智能、安全和便捷的出行体验。科技打破了由价格构筑的消费壁垒,实现了体验的“平权”。
同样,国产智能手机的崛起,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用千元机流畅上网课、看高清视频、使用AI翻译工具;国产家电品牌如美的、格力、海尔,把带自动清洁、双变频技术、一级能效的空调,从一二线商场专柜,以同样甚至更低的价格送进云南、贵州的乡镇家庭。
这就是科技解开“地域税”的第一把钥匙。
而在模式上,绕开传统的经销模式,打造“工厂—门店—消费者”的短链体系,成为解开“地域税”的第二把钥匙。
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,硬折扣模式。
我在日喀则遇到的这家“零食有鸣批发超市”,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硬折扣超市以前有一个绰号,叫“穷鬼超市”,因为它是伴随着危机诞生的。
19世纪,美国工业严重过剩,尤其是到了大萧条,库存堆成山,老百姓却穷得买不起。商家为了清库存各种斗法。
有些脑子活泛的商家,开始向员工和消费者打折出售库存,后来就有了工厂直销店和折扣品牌。
接下来,这套玩法又被德国和日本学了去,因为这两个难兄难弟都经历了经济崩盘。比如日本在90年代泡沫破裂,平均GDP增长不到1%,但百元店业态却能逆天改命,大创、Seria等品牌一路崛起。
不过,这种折扣店属于软折扣,卖的是尾货、次品、退货这类非标品,打折是暂时的、清完就没了。有点像现在的“百亿补贴”,属于特殊操作,非常态。
那么,既然有软硬之分,硬折扣又硬在哪里?
三
硬折扣的低价,不是靠偶尔甩卖,而是一套长期稳定、甚至有点“偏执”的运营策略。
它是怎么做到的呢?
答案是重构价值链,这是一场关于“效率”和“利润”的权力革命。其核心就是去中间化、缩短环节、减少周转,并对各个环节的“钱”进行合理分配。
价值链重构的目的就是打造一个更短、更平、更快的系统,在这个系统里,每一分钱都花在了真正创造价值的地方。
除此之外,它还通过降低物流仓储损耗、提高人效、发展自有品牌等方式,从根本上优化成本结构,从而实现“高品质、低价格”的商业模式。它卖的不仅是商品,更是一套效率解决方案。
靠极致效率实现可持续低价,才是其不可动摇的核心。
通俗理解,软折扣像一个销售高手。它说:“这些东西原价很贵,但我现在搞活动/清库存/断码了,赶紧来捡便宜!”
硬折扣像一个效率大师。它说:“我重新设计了整个系统,用最聪明、最省力的方法,天天都能给你最低价。”
熟悉硬折扣的朋友,一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,传统商超血流成河式促销,打七折、七五折,依然门可罗雀;而硬折扣超市偶尔一场八八折,却人潮汹涌、场面火爆。
比如零食有鸣这种硬折扣零售品牌,平时从来不打折,只是每个月6号有一个“会员日”,会员日当天部分商品参与8.8折优惠活动,且只有会员可享受。
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底层逻辑的差异。
硬折扣超市不玩文字游戏、不搞频繁调价,它用常年稳定、实实在在的低价,一步一步凿穿了消费者的心理防线,建立起坚固无比的信任城墙。硬折扣不仅是信任的结果,更是能力的结果。
它卖的不是货,是确定性;它打的不是折,是利他主义。
利他,是消费平权与硬折扣最大的契合点。
大家读文章,别光看个热闹、听个故事。真正有价值的,是现象背后的那套大逻辑。
你得保持对经济生活的分析力。不管什么模式,能跑出来,一定是有它的生存土壤和规则。
这一趟跑下来,我明显感觉到,向西的经济辐射,藏着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。它的底层动力,就是消费平权。
你可能想象不到,日喀则地区面积相当于内地一个省,总人口却只有81万左右,是真正的地广人稀。但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,“零食有鸣”却成功撬动了一年超过一个多亿的消费和营业额。
说到底,硬折扣这个模式,从出生那天就带着“消费平权”的基因。
我们前面讲了西部是消费的“价值洼地”,这也让它成为了消费平权的主战场。
那么,硬折扣如何击穿几千年的地理屏障,实现东西同价的?
硬折扣企业之所以敢在不同能级的城市,几乎定出相同价格,背后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底层能力。
一是供应链的“精兵简政”。它们像打仗一样,砍掉冗余品类,聚焦几百个爆款单品。每一款商品,不论在西部县城还是上海社区,都来自同一供应商、同一生产线、同一批原料。通过大规模集采,死死压住出厂价,从根源上杜绝“因地定价”的可能。
二是物流与仓配的效率革命。它们建立起一张精密如战时补给线的物流网络,区域大仓辐射、配送路线优化、托盘化运输全程贯通。哪怕一包饼干要发往青藏高原上的小店,走的也是标准化、高频率的干线物流,成本被压缩到极限,效率却提升到极致。
今年8月,我去过零食有鸣公司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机器人智能仓,被震撼到了。
自动分拣输送机、机械臂、四向穿梭车、AGV机器人……货物从入库、存储到出库、分拣,全流程智能操作,自动送货到人。
这个仓库,一天发8万件货,一个月直奔200万件,能喂饱200家门店。
像这样的仓库,零食有鸣公司光在四川有五个。算下来,整个四川一天轻松发送35万件以上的货出去,这只是日常操作。
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它们家的货值并不高,一箱货平均还不到70块钱。就这种超低货值,居然还敢上全自动化系统。可以说,这对物流中整个仓、拣、配环节的降本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。
据对方透露,他们物流成本,只占到总营业额的2%出头。
凭什么?核心靠三点:量大,周转快,效率高。正是这三项叠加,才把成本优势压到了极致。
第三是极致数字化的运营管控。从采购下单到货品上架,全部数字化。系统实时监控数千个SKU的动向。哪些好卖、哪些滞销、该补什么货、该砍什么品,全部以数据和算法为依据。人不再凭感觉做事,而是依托数据打仗,全国门店如同一支高度协同的军队,整齐划一、精准响应。
而且,零食有鸣公司的极致数字化的运营管控,不止是对“品”(商品)的数字化,而是对“品”、“人”(员工)、“店”、“客”(消费者)的全方位数字化。
第四是硬折扣企业从一开始就立下死规矩,全国统一定价,绝不二价。这看似放弃了高消费区域的利润空间,实则换来的是老百姓的铁杆信任。一旦用户形成“这家店就是不骗人、一直便宜”的认知,复购率、口碑传播和品牌忠诚度会彻底爆发。
而这一切系统能力,最终都要指向一个核心命题,那就是真正满足消费者对“质优价廉”的全方位需求。
社区和下沉市场依然存在大量“品类刺客”,如烘焙、低温食品等,日用快消品的供给仍严重不足,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。
也正因如此,“零食有鸣”公司在此前的“硬折扣零食集合店”的基础上,于去年6月推出了升级版的“零食有鸣批发超市”,新增了米面粮油和调味佐料、纸品卫品、日化家清、生活百货等品类。最近,“零食有鸣批发超市”率先在成都等城市试点全新的4.0融合店型。这些门店进化成了真正的“社区性价比生活站”:新增当日现烤烘焙区,推出3.9元两个的酥皮蛋挞、2.9元一个的爆汁肠丹麦可颂;设立了热气腾腾的熟食柜,供应6.9元一个大鸡腿、1.9元一根烤肠、1.5元的包子以及玉米、茶叶蛋;甚至推出现磨咖啡,美式4.9元、拿铁5.9元等等。
看起来,他们要用实打实的低价鲜食,轰开下沉市场最后一道消费壁垒。彻底否定传统零售“看人下菜碟”的定价模式,抹去了地域带来的价格歧视。让小镇青年和大都市白领,真正站在了同一张价格表前。
这才是消费平权最硬核的体现:没有妥协、没有差别对待,只有一套通行全国的、毫不妥协的公平价格。
它不是优待谁,而是不轻视任何人。
四
现在大家基本能够理解,为什么说只有硬折扣,能真正实现东西部消费平权了吧?
在日喀则,我和他们的店长聊过,光是在西藏,零食有鸣公司就开了近200家店;全国总店数已经5000家,其中批发超市就有3000家。
已经是西部零售当之无愧的第一。
零食有鸣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,很大程度上,是走对了模式。
它用极致效率重构了流通链条,让品质商品突破地域与价格的壁垒,真正走入西部百姓家。
说到底,这场横跨东西的“消费平权”,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某个企业,它既是“硬折扣”这个模式本身的胜利,也是利他精神的胜利。
零食有鸣公司恰好踩中了节奏、做对了动作。
因为真正的推力,从来是模式背后的效率革命与时代需求。
于是,当高原小镇的货架,变得和沿海都市一样丰富;
当偏远牧区的孩子,也能轻松买到一杯好咖啡、一块新鲜面包……
这背后,是一条用数据、物流、供应链与战略眼光铺就的“平权之路”。
它不声不响,却正在重塑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。
从日喀则到那曲,从山南到阿里,它真正走进了每一个需要它的角落。
商业不只是流转货物、赚取利润,它还可以是一种温暖而坚实的力量。
向西,不仅是市场的拓展,更是中国从“江河时代”迈向“陆域全域时代”的必然进程。
也是一场深刻的东西共荣与文明进阶!
发布于:四川省配资平台股票行情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